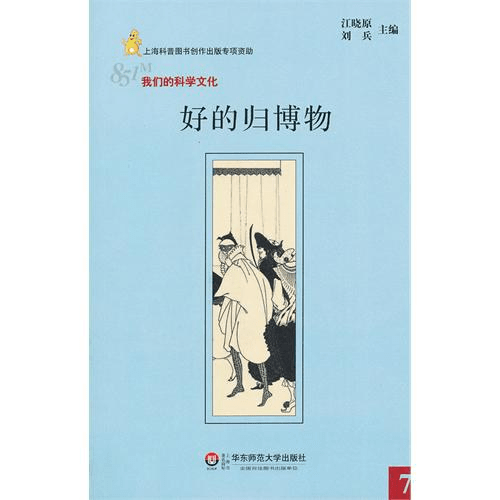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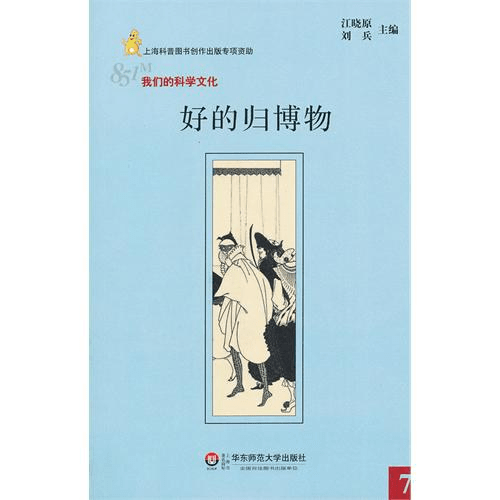
文章来源:《我们的科学文化-好的归博物》
原文地址:https://site.douban.com/141750/widget/articles/6769293/article/17025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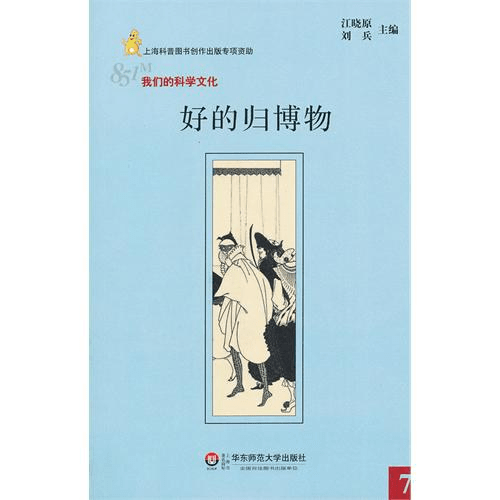
过去三十年间,我的研究常围绕中医进行。无论在北京或芝加哥,当人们听到这句话时都常常问:
-你信中医吗?中医科学吗?
-我的回答则是:你信西医吗?西医科学吗?
这些问题究竟有何含义?我们为何会问?这就涉及几个重点:
-信念和知识,信仰与科学的差别为何?
-“中医”(CM),“西医”(WM)这两顶大帽子里装得到底是什么?(我今天无法详细阐述,但这个问题我们总应去思考,并且给予它历史的解答。)
今天我讲的主题并非有关中医和西医这两个大概念,而是关于任何医学在历史、哲学、社会学中体现出的特殊问题。这里所讲的“医学”(medicine)是一个泛泛的概念,包括临床机构、专家社群、医学培训以及群体医疗记录。
要探讨医学的科学性和知识性,一种方式是强调它的客观性。我将以一个故事来说明。
1980年早期,有一段时间我在某个中医药大学学习。在那段时间中,我曾跟随一名德高望重的外科医生,观摩他的肝炎门诊。观察了几星期之后,我感到他在处理病患症状时所使用的方法是前后一致、很有规律的。他几乎总是诊出肝功能失调,他所看的脉象总是弦脉(strung pulse),他开出的处方则总和写字台玻璃板底下压着的那张处方一模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工作风格既不令人惊讶,也不引人警惕。几乎所有经他治疗的病人都已经在西医的医院中诊出了肝炎,所以他对于肝功能的诊断在每一个病例中都是正确的;他所开出的药方也许能够有效治疗最常见形式的肝炎。但是在我看来,他的临床工作毫无想象力和创见。此外,他的工作看起来也并不科学,因为他缺乏好奇心,去探究每一个病人患病的具体情况。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这位医生。在我们的交谈中,我告诉他我正在一门课中学习切脉。他非常开心,觉得自己逮住了一个机会来好好教育我这个无知的外国人—而这个外国人在他看来是非常倾向于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啊,脉象啊,”他说,“脉象是中医客观性最好的体现了。毕竟,它们就在这儿!”他一边说,一边将三个手指搭在另一只手腕上,“我能感觉到它,你也能感觉到它,这不是什么秘密,也不是什么个人体验。”这么想的不止他一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述中医科学性的说法广泛为人接受。另外,请注意对于这位医生来说,科学与客观是一回事。
为什么他想强调脉象的客观性?事实上,我注意到这位老关医生的学生们的做法—特别是在他不在诊所时—与他并不相同。我猜这些学生们所注意到的和他所注意到的并无二致,但学生们想得更多,记录的脉象也更多。换言之,即使在同一家诊所,任一临床病例的客观真理也都存在着争议。
有关西医的客观性,我将援引Ludwik Fleck的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一个科学事实的创立与发展》1)第120-121页的内容。
在一个医疗史学会议上,与会者就一个历史案例进行讨论,研究能否根据一个老处方做出现代诊疗。其中一位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文献中的方法与今法迥然不同。另一位则称复原诊疗总是可能的,因为疾病本身是不变的。我们只需从文本中建构出图像,就能够做出现代的诊断。第一位发言者反驳说,尽管疾病确实是不变的,但应对方式古今不同,而且从文本中也无法简单地建构出图像,因为文中充满大量的情绪化词汇,描绘那疾病有多严重,多恐怖,根本没提到如何治疗它,我们甚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发烧。
接踵而来的活跃讨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奇怪的是,一个基本论点在整个讨论中都受到维护—疾病本身是不变的—但会后,第二个历史学家却承认这是个失误。第一位史学家在争论中随随便便地确认了它,使得这一错误论点受到强化并最终为人接受,成为无可辩驳的公理。当会议结束时,没有一位与会者愿意付起承认这一论点的责任。
这个故事的要点如下:
疾病本身是不变的—肺结核总是肺结核,肺炎总是肺炎。
但是对疾病的检查,应对和描述是有差别的。
疾病本身被当做一个整体,一个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而为人接受(但是却没有人愿意为这一论断负责)。
那么,人们能否对作为自然实体的疾病作出诊断?人们能否精确反映或再现固化了的现实?
我们总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对于各种现代医学来说。客观性总与对世界的正确描绘密切相关。我们认为,科学以各种观点描绘了一整个我们所共享的世界。正因为科学知识在形式上超越了没有恒定形式的主观描述—这些描述充斥着科学史—科学就是客观的。而正确地对现象进行描述正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科学的基本任务。
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这一关于描绘与再现的偏见历历可见。例如,在Ian Hacking的经典著作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表象与干涉》2)中,他提到科学调查总是由两步组成:无论处于何种范式下,现代科学总是(准确真实地)先再现现实,然后在再现的基础上提出干涉的方案。他进一步指出,事实上,这两步彼此影响,互为渗透:对于干涉的限制影响到我们再现现实的方式,而干涉的成败能够检验对现实的描绘是否准确。
以上了解基于经验。对于医学来说,我们常将临床经验当做为了开出药方而对事物进行的基本科学描绘,临床产生的问题则被当成伴随着基础科学的再现而产生的难以处理的新事物。
Hackings的讨论虽然有用却所行不远。我们所需问的是,是否有必要完全以精确再现现实来定义科学,是否应当只将临床当作一种科学应用,一种对科学描述的检验。也许还存在其他方式,能够让我们在看待科学史时,将医学史与中医史囊括得更为和谐完美。而这就涉及到对客观性的彻底考察。
为了与这些相当现代的科学客观性的假设相匹配,我们将以特殊的方式对科学史进行处理。就算研究对象是近代社会,我们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也仍是对现代科学有意义的造物。比方说,开普勒的现代传记只强调他对数学,光学和天文学的贡献,弱化他所做的大量占星及占卜工作。占卜意味着解决个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近似于临床医学。因此我们可以说,开普勒最贴近现实,最符合临床知识的学问—占卜—被科学史束之高阁。
与此相似,李约瑟及其历史学家同僚在研究中国占星史时,强调的是精确的天文观测,严谨的记录保存和—最重要的—占星数学。他们更新了我们对于中国最早的科学家们所取得的技术成就的史学理解。但是,他们却将通书(Almanac)及用来占卜的历法及天文学弃置一旁。
李约瑟们处理中国占星史的方式并不符合历史。从皇家仁慈统治的“天人合一”到寻常百姓选定婚嫁吉日,在中国(以及近代欧洲),每个阶层都用得到历法。
我刚刚所讲的概念都有其价值:皇帝必须利用已知的时令、天象来好好统治;百姓必须通过选定好日子来确保一切顺利。也许您看过农历通书,其中的每一天,每一段时间,一个人与时间的每一种关系都与吉凶之兆相连。在这一历法科学中,每一种描述都附加有价值元素。时间本身既满载希望,又充满威胁。
这一切是否使历法不科学?今天我们这么说。今天我们说天文学是科学,而占星术是迷信。通书唯一“客观”的部分就是它所描述的可观测的日月运动。但是,在其古典形式(也就是今天的流行形式)中,日月运动的信息与影响人间祸福的因素休戚相关。人们使用天文信息是为了算命。通书提供了将人们与特定时令相连的技术,它的大部分技巧是通过将人的位置与空间相联系,或将诞辰合于宇宙时间的洪流而实现的。只有现代人才认为时间是抽象空洞的。对于全世界生活在现代之前的人们来说,时间都具有强大的力量,必须被驯化使用。通书的技术帮助其使用者在所有过去的时间中将特定时令与自我、家人及村庄相连。
刚刚所讲的,是天文史中关于“天”的实用知识常被人束之高阁。我们试图理解的,往往只是科学史中看上去科学的那些片断。医学史也是如此。人们只追寻生化知识,忽略了所有西方生物医学出现之前的诊断及治疗知识。将科学再现与临床干涉相区分的做法,在医学史中甚至比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中更为重要。人们似乎认为,为了从伪科学与江湖庸医手中保护弱者和病人,他们必须拒绝一切过去的医疗行为。在许多人眼中,中医只在一种条件下是科学的—当它的知识能为科学实验所验证时。
现代科学机构所习惯的分野是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相区分。我们倾向于认为基础科学更“客观”,更少受到人类某些“主观”因素的影响。基础科学据说能够更准确地再现自然,它所描绘的图景不会受到个人兴趣的扭曲。好的科学方法应当帮助我们看到真正存在的东西,而非我们以为,或希望存在的东西。
但医学并非基础科学。它局限于特定阶层的利益和需要。我将给出一个反例来说明这一点:
很久以前,我认识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他主要的研究都属于基础科学。他同时也是一位医生,从医学院毕业后工作了几年。从儿时起,他就对植物学和昆虫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同父母一道做了许多有关植物与昆虫的实地考察。他告诉过我一个在医学院发生的故事:在学习皮肤学时,他和他的同学们被皮肤的真菌感染吓坏了。教科书上的彩照展示了人体受真菌感染引起的疹子和脓疮,其状之恐怖令人不禁对拥有这些伤口的病人心生同情。但是我的老朋友却说,看到这些照片时他想到的是关于真菌的知识。他说,真菌的生命依赖于各种因素:它的孢子必须由风传递到温度、湿度、营养都刚刚好的地区,才能活个一两天;如果条件不合适,它根本长不出来。他向我解释了真菌的生命有多么脆弱,并且说,“毫无疑问,在皮肤学课堂上我总是站在真菌那边的。”
他是在开玩笑,但这个玩笑耐人寻味。他所接受的训练要他成为医生,他应当关怀的是人类的伤痛。但他所暗示的是这些真菌应当在那些恐怖的伤口中繁衍,因为它们的生命更加脆弱。他所感兴趣的是整个自然范式,而不仅是人类经验的范式。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位基础科学的科学家所应具有的态度,却不是一名医生应当抱持的立场。
但这种自然观不应当在真正的医学背景下存在。医学所需的知识总由人类的需求而定—毕竟这是个人类主导的世界。乔治·康吉昂(George Canguilhem)在几世纪前就通过他的重要著作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正常与病态》3)强调了这一点。他的论证很复杂,概括来说就是:科学史及事实知识表明,正常状态并非自然,而在人为。此外,他还论证说病理学并非自然科学。
这意味着什么?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回顾我朋友的皮肤学课本来说明。课本所展示的伤口,是从病患角度及医学角度所见的病变。但是从真菌的角度讲,那些伤口是它们繁茂所需的自然环境。对于真菌,伤口有益健康;对于人类,伤口则属于病态。
医学当然要站在患者一边。医学研究试图发现的,是如何更成功地打断真菌的生命之链来抗病。医学研究本身就始自普通人不科学的判断:所有人类的不适都应当被理解为病变。有病时,不需任何医学训练,我们也知道自己生病了;因此才有病人蜂拥进诊所要求医生治病。许多种类的医学都通过病理学与生理学来回应人类的病痛。生理学似乎描绘的是人体的正常状态,病理学则描绘疾病产生的条件与过程。
这些是科学吗?也许。生理学和病理学是客观再现自然的科学吗?我不这么认为。皮肤学仅仅在真菌给人带来危害时才会讲到真菌的生命之链;若人们能够有效控制真菌感染,就不会再有任何医学研究以真菌为主题。医学知识总是充满偏见地局限于自然界的小小一隅—人类的身体。正如天文与占星,科学与医学存在,同样是为了介入人们的生活,或是将人们与自然界以更祥和有利的方式相连。
让我们回到讲座最初的问题。人们问我“信不信中医”。我从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才好,因为我不知道关于中医应当信什么或者不信什么。中医并不能针对疾病或自然,客观再现身体;中医拥有系统化干涉疾病的各种技巧;中医拥有大量受欢迎的医师,遍布中国及世界;中医医师受过训练,以前辈医师的经验为基础;中医对我,对你,对病人的影响不容置辩;中医的技巧无法治愈一切疾病;中医也没有像宗教一样,提供全面系统的世界观。
如果人们问我,中医是否客观?针对我那位诊脉的关老师,我会给出否定答案。为什么?因为客观真理是所有医学及科学都不能够满足的梦想。
那么,让我们再问一个问题:我信不信西医?对许多现代人来说,这个问题近乎荒谬,因为生物医学不需要信仰。我们倾向于认为它客观真实。但如果真有人这么问,我的回答将毫无二致:西医并不能针对疾病或自然,客观再现身体;西医拥有系统化干涉疾病的各种技巧;西医拥有大量受欢迎的医师,遍布中国及世界;西医医师受过训练,以前辈医师的经验为基础;西医对我,对你,对病人的影响不容置辩;西医的技巧无法治愈一切疾病;西医也没有像宗教一样,提供全面系统的世界观。
所以,我会说,我们所有人都应当既信西医又信中医。如果我们以客观来定义科学,那么每一种医学都将被划出科学知识的范畴。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定义科学?“主观的科学”听起来有些荒谬。事实上,纠缠于主客观并不能使我们获益。我们也许应当将注意力转向现实世界,其中的人类(而非真菌)努力对疾病加以干涉。无论我们看待医学时是作为病人、史学家、医生或哲学家,我们都可以绕过那些作为科学特点的客观再现。让我们将医学当做一种艺术,一种技艺吧;让它成为一个实用的领域,专家与病患一同致力于解决问题,所使用的方法与进行的观察都既主观,又客观。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