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源于英国纪录片《电子游戏如何改变世界(2013)》,该片在回顾全球经典游戏的同时探讨了游戏的演变过程,分析游戏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文章来源:2020年12月25日《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游戏正向价值专栏第一篇
原文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VNFr8-xcBPU9wGv3REqbTw
2020年10月14日,人民网在游戏责任论坛上发布了《中国游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腾讯、网易、三七互娱、完美世界、多益网络、字节跳动等公司纷纷到场,并且不再强调自己所制造的游戏的经济价值,而是更多地讨论游戏企业对社会的影响:游戏企业如何尽行业责任?游戏行业如何推进行业自律与标准化建设?游戏如何表达传统?
这次会议,是一个重要的符号,标志着游戏作为一种媒介正在成熟之中。它不再强调自身创造的经济奇迹,而是开始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社会影响。
这看起来也许难以置信——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从2020年游戏产业2308亿元的产值、6.4亿玩家的覆盖率来说,游戏似乎早就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了。然而,实际上,从它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来看,游戏似乎还更像是一种亚文化——游戏中的许多术语,大众仍不理解;而从媒体报道中来看,对游戏的展现仍充满了不熟悉其内部机理而造成的偏见之论:认为游戏是电子海洛因、是成瘾媒介、坑害青少年成长的言论仍为主流。
整体而言,我国一般大众的游戏素养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人们仍不清楚游戏的本质,不清楚游戏应当如何分类、如何利用,也不清楚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它对于人的吸引力,以及它造成的社会影响。
我们似乎很难接受一个观念,即游戏是一种需要花时间去理解、研究的媒介,是一种需要磨炼开发技艺(craft)的表达方式,是一种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之声,并持续地塑造着我们对于时代的认同与理解的数字文化遗产。
各行各业的职业人士,无论有没有玩过游戏,似乎都有资格对游戏说三道四;每个人都有“我/同事/邻居家的孩子”被游戏毁掉的故事要讲;每个人都可以呼吁“禁掉游戏,救救孩子”;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似乎都可以给游戏领域以批判和建议。
当我们明白文学批评是一个专业,影评是需要有观片量和影视理论做基础才能进行的时候,我们社会对于游戏的这种态度似乎就额外奇怪:为什么对游戏的认识,就对专业性没有要求?一个没有玩过游戏,也没有研究过游戏的人,凭什么成为评判游戏的“专家”,给家长与青少年以种种高屋建瓴的指导,甚至以电击或其他极端手段来“治疗”玩家?为什么我们在面对其他媒介的时候,都能科学、理性、平和,却唯独在面对游戏时,永远都愤怒、恐惧、偏执?
这首先大概是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本来就对游戏充满偏见。我们的二十四史中,充斥着“君子不戏”的判断:游戏的人,是昏君、佞臣、仆、妾、奴,没有一个是好人;对他们的社会评价,也是消极评价远大于积极评价。甚至我们所使用的关于游戏的字,无论是“嬉”、“戏”、“玩”或“耍”,也以打入家庭领域的女字旁为主,竟没有出现一个人字旁的字。如果我们细读每一个字,就会发现,两个和游戏相关的女子旁的字,“嬉”和“耍”,本身都具有贬义色彩。究竟是女字旁带来了贬义,还是因为贬义才用女字旁,我们不得而知;所能确证的,是表达游戏概念的汉字里,四个字有两个字本身有贬义,另两个则逐渐发展出了贬义的含义。
词语是观念的载体,但词语本身也在传达观念。若我们使用的描述游戏的概念都带有偏向性,如何还能中性地认识游戏?而破除我们对于游戏的偏见,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让游戏的社会影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游戏是什么呢?它首先是一种媒介。和其他媒介一样,游戏能够记录这个时代的痕迹,也可以承载这一时代的表达。也和其他媒介一样,游戏从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性。它既以规则的形态凝聚了一个时代最根本的特点,是一种强力的时空胶囊,也是本世代年轻人的社交场。
我们从最流行的游戏之中,往往能看到时代之声。在九十年代与千禧年初,我们有《大唐诗录》、《幽城幻剑录》、《阿猫阿狗》、《武林群侠传》和《中关村启示录》,他们都是单机游戏,创作者的喜好与心声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达,从题材到机制都有探索与创新,也往往不吝于对玩家提出挑战。这也是开放的时代精神的折射,开发者将自己熟悉的中国文化与游戏有机结合,探索着“中国身份”;玩家愿意接受挑战,愿意在游戏杂志上刊登的攻略的帮助下攻克开发者留下的难题,像享受好的文学与影视作品一样,享受游戏能带来的审美体验。那时的游戏是无关输赢的,大家享受的是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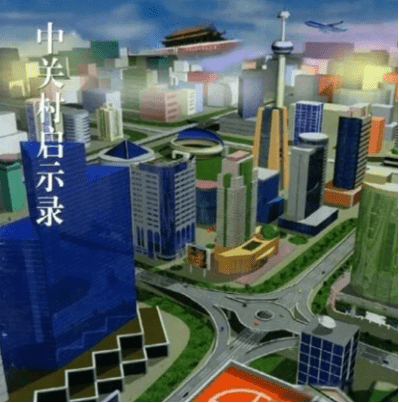
▲《中关村启示录》是早期的一款国产模拟经营游戏,在游戏中讲述了“中国硅谷”中关村的企业发展史。
十年过去,随着移动游戏时代到来,流行的游戏变成了另一种:无论是《王者荣耀》或者是“吃鸡”,都是快节奏的社交游戏,而且遵循着越来越严酷的逻辑:王者荣耀中还可以有一队玩家取得胜利,到了“吃鸡”,一百人中,只有一人能赢了。这无疑是一个资源匮乏的社会中越来越激烈的社会斗争的展现。
除此之外,我们从流行游戏之中,也能看到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一种“没有时间的万神殿”的结构正在游戏之中逐渐形成。比如,在最具代表性的《王者荣耀》之中,来自不同时代的历史与神话人物齐聚一堂,以5v5的方式同场竞技。这种历史感的消解,既受到MOBA游戏机制的影响,也是时代追求“更短、更新、更生动”的表达的直接结果。注:MOBA(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 Arena)是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的简称。MOBA游戏有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Dota2》《英雄联盟》等。
诚然,不同的游戏机制适合于承载不同的内容,但从游戏的社会影响而论,我们也更希望能有更多适合承载深度文化内容的游戏出现,像将《长恨歌》嵌入在游戏中、带来了高级文化体验的《大唐诗录》、或是生动展现出我国九十年代电子产业发展状况和时代精神的《中关村启示录》,或是表达出中国普通人成长体验的《中国式家长》一样。

▲《中国式家长》模拟了一个中国孩子从出生到高考的这一段成长历程。
上个月我在上海的独立游戏活动上说,游戏创作者们也许也需要一次“现实主义运动”。因为只有让游戏去传达社会中的普通人的爱、痛与关怀,游戏才能成为普通人表达的媒介,也才能从现在处于亚文化地位的状况中挣脱出来,成为真正的大众文化。

我们在学界呼吁游戏改变世界,其实已经很多年了。从《游戏改变世界》这本书在中国出版起,游戏化领域在中国也存在了将近七、八年了。但是我们真的看到有游戏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吗?小规模的可能有,大规模的真不多。可能最积极地与社会产生了关联的游戏化产品就是蚂蚁森林,它确实地让普通人可以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公益的环保行为相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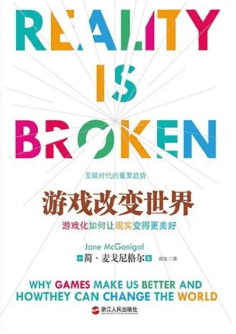
▲图为《游戏改变世界》书籍封面,该书作者简·麦戈尼格尔(Jane McGonigal)是著名未来学家、知名游戏设计师,她曾被《商业周刊》誉为“十大最重要创新人士之一”。
游戏产业的产值非常可观,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有许多人是真的通过游戏在维持自己的社交关系,加深对于自己朋友的理解,也通过游戏缓解了一些心理压力,特别是在《动物森友会》这样的游戏中。

▲任天堂公司开发的模拟经营类游戏《动物森友会》在年初爆火,由于疫情被困家里,不少人因为动森获得了快乐,在游戏中建设自己的小岛。
但动森这样的游戏,也不是现在最赚钱的主流游戏;现在最赚钱的游戏,还是氪金抽卡的游戏,它的赌博性远强过游戏性,它的核心甚至就是消费系统,游戏中的画面、音乐、主题等等表达性其实是很弱的。这种游戏能改善世界吗?我觉得真的是要画一个问号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思考游戏改善世界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它与游戏产业发展的现状并不是完全正相关的。这样的主题,需要更多地与游戏相关的公益行动,需要更多的研究,也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来对游戏做科学、严谨的游戏批评。
我们这一期在组稿时,除了理论方面的考量之外,更多地其实是从实践的角度在选择合适的案例,希望这些只在小圈子中为人所知的,尝试用游戏改善世界的案例,能为更多人带来更多关于游戏的思考。
例如我本身也参与其中的《游戏星球》的纪录片,尝试结合治沙与游戏,以社会实验的方式来探索“游戏能否改变世界?”的主题。目前游戏x社会的gamejam也还在开放地向社会征集提案,这也是一个试图吸引更多公众来参与的过程。注:gamejam指一场48小时的、基于某一主题的游戏开发黑客马拉松(Hackathon)

▲游戏星球拍摄期间的游戏开发活动
此外,专题中也有向在国内做游戏艺术展的艺术家邀约,希望能产出一些游戏作品与公众联结的内容。游戏与社会公益、游戏与教育、游戏与社会组织、游戏与未来等主题,也在我们的译稿中有所体现。
实际上,在参与和游戏相关的社会实验的过程中,我本身有一个非常痛切的感受,就是游戏如何发挥社会影响的这个问题,有太多环节缺失了。
游戏要如何定位,它怎么影响社会,它适合做哪些事、又不适合做哪些事,可以看到人们现在也仍在探索。比如说,是不是只有功能游戏才能有社会功能呢?商业游戏能否有足够多的积极社会影响,又要如何发挥出来呢?是否只有玩家才能被游戏影响,还是实际上所有人都能被游戏改变?从影响社会的行动来说,是否只有做游戏和设计游戏,才能算是游戏影响社会?政府、院校、公司、公众,每一个环节在游戏影响社会这件事里,都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和游戏相关的公益项目,要怎样才算是可持续?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和游戏的社会影响相关的项目,只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否足够?我们又应当如何、以何种尺度去评价那些在造成社会影响的游戏?这个专栏提出的问题可能远多于它回答的问题;但它最大的价值与贡献,也许就在于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开始能够看见游戏与社会结合时,那些巨大的潜力、可能性与巨大的问题。
Leave a comment